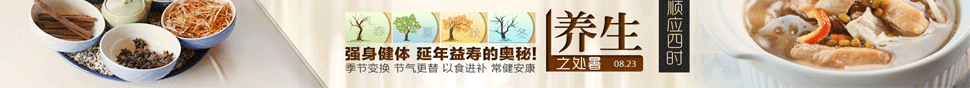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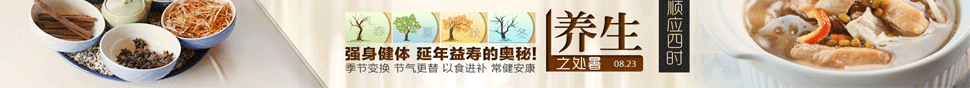
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被翻拍成电影。
最近海报释出,尽管依旧又纷纷争议之声,人们还是难免心头留有期待。毕竟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单从故事本身,就极具魅力,写尽了人性的苍凉和凄苦。
葛薇龙一直想要回到上海,但却被香港绊住了脚,最终把灵魂卖给了这座城市。
在这个故事里,上海是葛薇龙一直想回,却回不去的故乡,也是天真的葛薇龙的象征,而香港,则是冰冷残酷的成人世界和未来。
《第一炉香》
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是上海女性,她本人在上海长大、在上海写作、在上海度过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前半生,她对这座城市的描写,也投射了她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和认知。这座浮华流动又饱藏暗垢的城,是她与世界对话的渠道。
张爱玲
但又何止张爱玲。亦舒在上海出生、随后又去到香港,王安忆写尽了这座城市的光面与希望,而就算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对上海的印象,也多少受到了郭敬明笔下对上海极尽奢华写绘的影响。
张爱玲写,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
这座城实际也如此,它的繁华与凄凉、温暖与冰冷,让它成为一个天然的试验场,也是天然的文学沃土,它的每一条街和巷、每一个楼和景,都变成了容器。
这座城里,藏着许多作家的矫情。
上海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很难说张爱玲到底对上海这座城市是什么感情,也或许她自己也讲不清楚。
她用冰冷而诡谲的笔调描写上海。《心经》开头写:那是仲夏的晚上,莹澈的天,没有星,也没有月亮……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
《第一炉香》
但是又难以克制内心对这片土地的倾慕。《易经》里刻画的城市不觉冰冷和异化,反而生出一种莫名的温柔:广大的老银器店,书法写的大招牌,招牌顶上还有金银细丝工,像新娘的头饰,夹在新店铺间。新店铺都是玻璃橱窗,单有一件连衣裙与时髦的照明灯。处处可见各种不同时代的外国建筑。红的黑的治花柳病的海报张贴得到处都是,倒使肮脏晦暗的建筑亮了起来。
她说,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
《色戒》
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特别的时代,政治和风月共存、大时代与世俗生活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割裂又融合。
张爱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宏大的时代放置又脱离出作品,用尖锐而又犀利的笔触,把故事营造在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氛围里,书写了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命运。
悲凉是底色,但是基于虚妄的狂欢,才是普通人的真实人生。她既写软弱风流的男人、也写虚荣势利的女人,既写生活在宅子里笼中鸟一般生活的遗老遗少,也写街头里巷、世俗又安稳的小市民。
她从不写英雄,只写虚弱的普通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
在那个旧传统与新时尚交替的时代,张爱玲的另类、犀利与刻薄,显得格外真实,又格外“时髦”。
她不写“虚伪的女性主义”,往往写的是真实的女性虚弱,她笔下的女性悲剧,往往是基于尊严,为了想要获得尊严而诞生的。不论是丧失尊严、丢失自我,还是迷失爱浮华之中,她书写的都是女性最真实的挣扎。
这种细腻冰冷、又有着瓷器一样易碎质感的文字,与那个时期的上海不无关系。
《海上花》
孤岛时期的上海,把上海的浮华破碎氛围拉满,也让文学史上关于上海,最特别、最风韵十足的一笔,留了下来。
张爱玲在美国过世后,余秋雨曾评价: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献给上海的金色赞美诗我们谈上海,往往谈的是“老上海”。
旧日老上海的韵味变成破碎的元素,流淌在人们对上海的印象里。
尽管很多人不想承认,但是还有一个新式作家对上海形象的新构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郭敬明。
《小时代》
郭敬明与上海这座城,有着他本人一样让人觉得激烈到恍惚的羁绊,具有一种不死不休的决绝。四川自贡的小镇青年,和远方浮华遍地的大都市,郭与上海的故事演绎的是新上海的风姿。
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让“老上海”逐渐成为回忆,高楼大厦逐渐取代了弄堂里巷,一地浮华以一种更机械冰冷的模式重新诞生。
旧日的城市肌理分崩离析,消费主义浪潮让这座城市隐藏的气质逐渐更尖锐地展现出来。
《小时代》
在中学时代的散文中,郭敬明就在倾诉自己对这个素未谋面城市的痴迷:我的根似乎是扎在上海的,就像人的迷走神经一样,一迷就那么远。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让不爱上海的人出生在上海?上帝一定搞错了……我的同学曾经在复旦大学里逛了整整一天,并且拿了很多照片给我看。我望着那些爬满青藤的老房子目光变得有点模糊,我想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这个远方的奇幻都市成为郭敬明的梦里故乡。
郭敬明微博
有人说,近百万字的《小时代》是郭敬明“献给上海的金色赞美诗”,《小时代》中的角色无一不体现了他对现实世界的渴望、对上海的渴望。
他在书中对人性的俯视和对这座城市的仰视,用极具他者化的视角塑造出了这个四川青年对上海的痴迷与憧憬。
“它仿佛是一个庞大的终极梦幻,也同样是无边的灰烬旷野。”他曾这样写道。
年时,北大教授张颐武曾在博客上将郭敬明列入上海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在张爱玲远去,程乃珊故去,而王安忆已越来越和上海年轻一代疏离而影响力淡化的时刻,郭敬明变成了上海想象的新的部分。”
他最后定居上海,把自己羽化成人们对上海印象中无数个标签中的一个,也成全了当年那个少年的一场幻梦。
时代、城市和人
上海这座城里藏着不止是作家们的呼吸,还有无数从过去到现在,普通人的。
前段时间《三十而已》中,三位女性身上无一不透露着对于这座城市代表的新世界的渴望。
我们也发现,在无数关于上海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意象,阳台。
临街的阳台与流水一般的街道、人群。
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曾经谈及,从阳台上,可以瞧见佣人提了篮子去买菜,还可以听见各种叫卖声。卖草炉饼的年轻健壮的声音和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喉咙唱起了对台戏,卖馄饨的则一声不出,只敲梆子。
对于世俗生活的俯视、逃离,以及渴望近在咫尺但又在远方的欲望,或许是阳台给人最真切的感受。
俯视生活,但又深入生活的肌理,在沉溺中将自己抽离。
上海是某种意义上金钱和欲望的化身,消费主义变身为精致的食物、建筑以及新派的生活方式,但生活又藏纳在寻常巷陌中、藏纳在孩子们的叫闹声、弄堂里的饭香味里,藏纳在每一个角落。
这样既虚且实的质感,或许就是上海的气质。极致的描绘往往营造出一种关于文学和生命的张力,演绎着人们对于生命意义升华的期盼。
张爱玲讲,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但她笔下的葛薇龙也正是在华袍中迷失。
有人把自己的梦想定义为征服一座城市,但往往渴望征服城市的人都被城市所征服。
张爱玲的作品无疑以力透纸背的笔触书写了这座城市的真相,但苍凉底色上的充满人性的挣扎和奋斗也是真实的。
如果要作比,北京的欲望感更虚无,上海的欲望感更真实。
这种真实的欲望穿着繁华奢侈的外衣,镀着金,但实际上还是一种充满了渴望的对未来的憧憬。
更美好、精致、熨帖的世界,那些金钱、物质变成一个个华美袍子上的精致盘口,在时代的晕光下折射出冰冷而又温暖的声音。
不是这座城市适合书写人性,而是这座城市演绎着人性。
郭敬明以《小时代》为名书写着自己对上海的想象,他身上强烈的代表性也象征着一代人的。
但实际上,不论是大时代还是小时代,关于上海的幻梦和传说只是属于上海。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只能把自己的情怀在这里寄居。
而真实的上海,不会因此而改变或者动摇。
撰文:青豆图片来源于网络编辑:吴司笛、调反唱唱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